如果你能預知死亡何時到來,你會及早向親友交代臨終意願嗎?有人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仍未有把握時間向家人表達臨終意願,結果令親友處理相關事宜時心力交瘁,更令年邁的母親出現失憶的應激反應。同樣知道自己隨時都有可能離開人世,有人會選擇坦然面對,及早向親友交代好臨終意願,令親友可在實務和心理上準備面對自己的離世。
對死亡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源自他們接受生死教育的多寡,生死教育藉了解死亡來反思人生,減少死亡帶來的痛苦和遺憾,因此生死教育絕對是人生中重要的課堂。近年香港關於生死教育的討論越來越多,生死教育工作者嘗試以不同方式向大眾傅遞生死教育資訊,但教育工作往往只依靠民間機構自發進行,欠缺政策支援的生死教育遲遲未能成為大眾的必修課。
避而不談死亡成反效果 及早預備可減親友痛悲
比起曾接觸生死教育的喪親者,從未討論過死亡的家庭在面對親人離世時會受到更大衝擊,吳小姐的大伯近月因癌離世,此事更令吳小姐的嫲嫲,即逝者的媽媽,出現失憶的應激反應。大伯在患病初期一直隱瞞自己病情,直至病徵已經十分明顯才向父母坦白,「兩老得知後看似沒有很大反應,其實內心十分擔心」,吳小姐表示嫲嫲更會躲起來哭。家人對大伯患病一事避而不談,更遑論商討後事安排,「大家都裝作沒事,但把他當作病人照顧,但不會說出口。」
直至吳小姐嫲嫲接到大伯的病危通知的電話時,她表現平靜,但家人回家後,發現她忘記了大伯患病一事,不停問大伯去了哪裏、是不是又出去玩了,她失去了大伯患病後的記憶,吳小姐指「爺爺說她接到電話後,突然坐在沙發上哭泣。」事出突然,家人叫她馬上休息,希望情況好轉,幸好她睡了一覺醒來後便回復正常,但卻不知道自己曾經失憶。

吳小姐一家雖然對死亡沒有很大的忌諱,但平日也很少談論生死話題,以至面對大伯患病時沒有共識,大伯亦從未與家人商討臨終安排。吳小姐形容大伯一向獨行獨斷,後期不配合治療又經常強行出院,回家後卻又經常暈倒,同住的年邁父母根本無法應付,造成家人的負擔。大伯臨終留下的並非美好的回憶,吳小姐憶述大伯離世前所發生的種種,感嘆「對兩位老人家和爸爸(逝者弟弟)而言,大伯因為不配合治療為他們帶來很多麻煩,他的離世可能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解脫,好像終於可以放下一件事,所以傷心之餘都有一種解脫的感覺。」
大伯臨終留下的並非美好的回憶,吳小姐憶述大伯離世前所發生的種種,感嘆「對兩位老人家和爸爸(逝者弟弟)而言,大伯因為不配合治療為他們帶來很多麻煩,他的離世可能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解脫,好像終於可以放下一件事,所以傷心之餘都有一種解脫的感覺。」
親人離世竟成為家人的解脫,積極推行生死教育的安寧服務社工梁梓敦指死亡對人的影響可由家庭推演至社會層面,「所以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想進行生死教育,我們相信死亡不單止是個人事務。死亡的發生是很個人,但會影響到家庭,甚至社會,即使未去到社會層面,也無法否定一個人的死亡會為家庭帶來很大影響。」

同樣面對疾病,患有罕見病克隆氏症、意識到死亡有可能隨時來臨的Eric選擇早作準備,向妻子交代自己的後事安排。Eric自患病起一直留意生死教育資訊,最近留意到遺體修復師伍桂麟經營的殯儀社企「一切從簡」舉辦生死教育工作坊,便與妻子Eva一起報名參加。活動開始時,Eric主動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情況,他於二十多歲時確診克隆氏症,克隆氏症屬腸道免疫系統疾病,現時無藥可醫,只能用藥阻止病情惡化。Eric向Eva提議一同參加生死教育活動時,Eva很感興趣,希望可以學習如何面對死亡和處理後事。丈夫患有罕見病,她坦言「因為可能有一日,不知道他會不會很快離開,(接觸生死教育後)起碼不會那麼傷心,到時只有自己一個,腦袋會一片空白,無法思考。」
Eric早已向Eva交代後事一切從簡,捐出器官和遺體,成為大體老師,希望可以在離開時幫助別人,Eva支持丈夫,亦認為大眾有必要表達自己的意願,「像我先生那樣,我也要思考我自己要怎樣面對,他的意向我都要知道。」二人得知是次報道的主題圍繞生死教育後,更主動積極地分享生死教育的經歷。

參加了生死教育工作坊的還有Tim一家三口,與Eric的經歷相似,Tim在2017年確診淋巴癌,幸好覓得良醫,加上父母一路陪伴他抗癌,他在2019年中康復,現時為觀察期。Tim坦言患病改變了自己對生命的看法,在醫院、癌症日間中心看盡生死,覺得死亡其實是很平常的事,「有時會想,下次未必見到這個人,可能不走運,做完療程後中風、器官衰竭,就這樣離世也不意外。」從不會思考如何面對親友離世的他,學會在心理和實務上預備死亡,「(以前)會到時才想,現在看事情會更加深刻,正正是因為經歷了這麼多,所以會思考不如我們提早預備。」

他的父母對生死議題的開放態度亦令Tim從不忌諱談論死亡,連參加生死教育工作坊亦是媽媽的提議,父母都認為人需要預備死亡,Tim的爸爸回想自己的妹妹因病離世,早已感受過死亡的可怕,後來身邊陸續有同事、朋友離世,令他覺得人需要預備死亡。Tim的媽媽同樣坦然,豁達笑說「要去面對和接受這件事(死亡),人的經歷就是這樣,這些事並不是你不說,就會遲幾年才發生。」
Tim的媽媽因為有照顧長者的經歷,認為及早向家人表達意願,令喪親者能夠依照逝者的意願送別他,不必為處理後事而徒添傷痛,更可以避免做成喪親者之間的矛盾。「如果不去討論傾後事,到事情(死亡)發生時,就會出現一些負面情況,金錢、儀式、處理遺產,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生死教育並非練成無懼心境 學習藉死亡覓人生意義
「預備死亡」聽上去好像很悲觀,事實上生死教育是希望大眾在心理及實務上預備死亡,令死亡變得較易面對。曾因病情嚴重而住院的Eric坦言,以前從未思考過死亡,天真地以為自己的人生會如大多數人一樣,安穩地生活。但患病令他失去健康和活動能力,眼見鄰床病友一個接一個離開,才覺悟死亡可隨時到來,「突然有一日,你只可以躺在床上,甚麼也做不到,無法舉手、無法喝水、無法入睡。」
Eric憶述那段卧病在床的經歷仍心有餘悸,與死亡擦肩而過,Eric直言自己「其實也不是不怕(死亡),但可以很坦然地面對(死亡)」。他從此學懂活在當下,他從容道「在世時與身邊的人做想做的事,對身邊的人好一點,大家難得聚在一起,相處時盡量好好享受。」
而Tim一家視死亡為人生必經階段,閒時說說壽衣要甚麼顏色、喪禮要怎樣操辦、有甚麼器官能夠捐贈、怎樣處理遺產等各種與死亡相關的事務,態度輕鬆的有如討論晚餐要吃甚麼一樣。Tim在患病後明白死亡總會來臨,但卻不會因此看重死亡,「時間到了死神call(召喚)你就call(召喚)你」即使在父母面對,Tim仍毫不忌諱地開玩笑說,他經常用這一句表達自己對死亡的處之泰然,問及三人對生死的看法,他們的答案出奇地一致:「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是老生常談,但卻未必人人知曉除「活在」當下外,要怎樣「活好」當下。青年教育機構HOBBYHK的創辦人之一的陳培興在機構中負責生死教育範疇,作為禮儀師的他反而更著重心靈導向的生死教育,他希望透過生死教育令人反思自己想怎樣過活。對他而言,生死教育的重點在於明白生命有限後,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裏找到自己的價值和人生意義。
陳培興藉分享禮儀師工作的見聞與大眾討論人生課題,如家庭關係、人生意義、人際關係、個人情感等,「比較關注跟他們(參加者)切身的事,或者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如關係、溝通,我們真正重視的事。」他憶述有一次到校進行遺書導讀工作坊時,有一位平日較頑劣的學生在遺書內提及一直留意到家人腳痛,但不敢表達自己的關心,又叮囑家人不要吃太多即食麵,因為不健康。他有感青少年內心細膩的情感其實需要這些機會來抒發,藉生死教育發掘這些平日難以表達的情感對參加者更為重要。

教育不再單一發放資訊 渠道多形式變吸引大眾
有見及生死教育形式往往較為單調,HOBBYHK於2021年開始舉辦「小組x生死x培訓企画」,招募對生死教育有興趣的青年,進行生死教育研習,最後舉行一場生命展覽。構想計劃的陳培興眼見社會上不多機會讓有志進行生死教育活動的青年體驗,他希望提供多一個途徑讓有志青年投入生死教育活動。


生命展覽作為計劃的重頭戲,學員會為主角籌備一場生前告別禮,呈現其人生經歷。上屆主角是一名癌症末期患者Tiffany,學員為她設計了一場模擬確診的體驗,帶領參加者以第一身經歷她面對的事,並以在各展區以相片、影片、文字等形式呈現她的人生。



計劃除了為學員提供實踐生死教育的機會外,更為學員提供了反思人生的機會,上屆學員Kelly指自己透過參與計劃中的活動,如收拾遺宅、旁觀喪禮等,令過去較少機會接觸死亡的她察覺死亡原來是那麼近,「死亡不再遙遠,令我反思生命裏甚麼值得捉緊、甚麼應該放開。」生死教育中的「從死看生」就在此體現,陳培興笑言對學員「沒有期望」,他認為只要大家覺得有趣、在過程中有反思便足夠了,因為開始思考就是生死教育的第一步。

本港亦有其他機構嘗試以不同方法積極推動生死較育,殯儀社企「一切從簡」除了會為大眾甚至社福工作者舉辦生死教育工作坊外,更在社企內附設生死教育書店。從事遺體修復工作的機構創辦人伍桂麟有感遺體修復只能修復肉體,無論如何都修復不到喪親者的內心,因此開始進行生死教育。他坦言書店在香港難以經營,更遑論專營生死教育相關書籍,堅持營運只是想為大眾提供主流書店外的另一選擇,希望為大眾推供多一個渠道接觸生死教育。






本港生死教育推廣不足 學術研究有助制定政策
生死教育在香港尚未普及,推廣之難更在於「民智未開」,陳培興經常到學校進行生死教育分享,但他留意到學校對生死教育的態度比較保險,「如果活動會牽動到學生的情緒,學校都怕『執手尾』,要安撫他們、輔導他們。」
他指如要進行心靈導向的生死教育,必定會牽動到學生情緒,有時候牽動情緒是好事,代表他們有深入反思,但學校卻想避免,「如果連這些也敏感到容納不到的話,很難進行心靈導向的生死教育。」事實上,陳培興到校進行的活動反應很熱烈,講座完結後學生紛紛舉手發問,可惜因時間所限未能讓所有學生提問,該校校長更表示學生對是次活動的反應比起平日更積極,反映他們對講座內容感興趣,能觸動到他們,甚至引起反思。


要在學校恆常推廣生死教育,必先令教育工作者和政府明白生死教育的重要性,梁梓敦指本港的生死教育推行步伐緩慢是因為香港沒有天災,死亡對大眾而言是一件很遙遠的事。他認為下一步便是學術研究,研究和量化生死教育的實際效果,「香港甚至全世界也很少人研究生死教育的實際影響,我都只可以籠統地告訴你有效,但有多大成效?能否量度?不知道,因為沒有人研究。」他期望未來建立知識庫,令生死教育成為正規恆常課程。
他續指如果生死教育要成為恆常教育,政府一定要制定政策,而政策背後緊扣的正是研究,如果沒有大量研究印證生死教育的重要性,政府是不會推行相關政策,「現時的生死教育都是民間階段,民間很多人進行生死教育,但我們上不到另一階段,我們憑甚麼去說服一些有資源、有權力的人?」當政府見到大水眾因不了解生死教育,欠缺準備,最終為醫療系統帶來負擔,政府才會意識到生死教育的重要,但現時未解釋到早期生死教育如何惠及社會,生死教育仍需要更多研究支持,才能真正走進生活。
《San Po Yan Magazine 新報人》
新報人(SPY)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生實驗報紙,以實踐新聞自由為原則;體現不趨附商業利益,不附從政治功利,只為專業學習的存在價值。

生前無用死後有用 製造在世有用的「遺物」

直擊移英港人生活 超市購奶類蔬果較港便宜 部分中式食品價貴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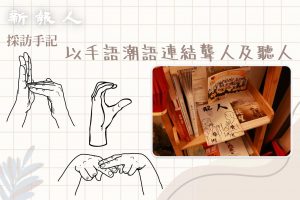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