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下以自殺者親友為主角的題目時,我本著希望可以透過這篇報道為正在經歷、經歷過親友自殺離世而哀傷的人們帶來一點力量的想法,開始了準備。採訪後,聽過兩個個案——Elaine和Steve的故事、安寧服務社工梁梓敦、臨床心理學家葉惠蓮和網上心理支援平台「念念不忘」創辦人Savina的說法,又寫稿時重新整理過受訪者們的見解。這些都一遍又一遍啟發了我對面對親友自殺和面對死別的看法,令我更希望讀者在看完這篇報道後可以獲得反思。
思念與哀傷 自殺者的生存痕跡抹不走
做了五個訪問,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五位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說出並沒有所謂「走出悲哀」。人們常說遇到傷心的事要「move on(不再沉溺於過往)」,但在哀傷的人的角度,尤其是遇上身邊的親友自殺,這種哀傷可以是永遠都無法磨滅的。所以可以改變的只有與哀傷共處的方式。
就如Savina引述的一句:「正正因為那份愛之大,所以帶來的悲傷才那麼大。」畢竟逝者生前大概和自殺者親友亦曾在這個世上留下了不少回憶,有甜有苦、有笑有淚,這些回憶都是活生生的。人們常謂人的一生會死去三次:第一次是停止心跳、呼吸,生物層面的死亡;第二次是葬禮,儀式層面被宣告死亡;第三次是直至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忘記了你,這才是「真正的死亡」。
親友自殺離世的哀傷不能完全抹走,那是因為逝者仍然在記憶中活得鮮明。Steve在訪問中說過,即使摯友葬於外國,他仍會在重陽節到香港的墳場坐一會兒,正正是因為他怕忘記。他並沒有仔細解釋怕忘記的原因,但我想或許是友人雖然已逝,但她在Steve的記憶中活得鮮明、歷歷在目。
兩個生命的故事 一條不易走的路
整個採訪當中,我尤其感激兩位自殺者親友願意向我分享他們的故事。作為一個聆聽者,聽他們的故事時,也會有千萬種感受湧上心頭的感覺,但那不是一場戲,而是真真實實的人生。我不禁去想他們到底如何忍著這種痛一路走來。
由於是第一次做這種要觸及人情感的故題,訪問時我尤其怕會觸及他們的痛處,激起他們的負面念頭。又怕最後要他們忍痛說完故事,卻無法表達出他們的處境,變相對他們二次傷害。但最後反而是他們安慰了我。悲傷、自責⋯⋯情緒五味雜陳,他們整理的思緒卻出奇地清晰,也讓我十分順利地完成訪問。
如梁梓敦和葉惠蓮兩位處理哀傷的專業人士所言,自殺者親友面對哀傷時,最重要的是他們是有意識地處理自己的情緒,方法可以有很多種,並無絕對。從訪問過程中可以看得出兩位自殺者親友對自己的傷感是有意識的,聽完二人的故事,再聽到兩位專業人士的說法,更令我對兩位自殺者親友心生敬佩。面對親友自殺離世這條路不易走,亦不知了期,但他們仍然努力走下去、活下去。
「不被允許的悲傷」 讓自殺者親友定義自己
在報道中,並沒有太多的篇幅可以深入處理有關社會看待自殺的風氣對自殺者親友造成的影響,不過或多或少可以從受訪者的話中看出一點端倪。
我以前在中學選修了倫理與宗教科。記得當時老師教生死倫理,談及自殺題目要如何答題。當然倫理並沒有絕對答案,合理即可。但作為「求分」心切的文憑試考生,最安全的答法還是:「自殺是逃避、不負責任的行為。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只有說人是『有權生存』,而非『有權選擇死亡』。」
採訪過後,我對於Elaine說弟弟自殺不是一件可以見光和值得說的事十分深刻。又回想起高中讀到自殺一課的答題技巧,令我再三尋思,自殺者親友的哀傷之所以「不被允許」,難道不是因為所謂的一些「普世價值」或「主流」觀點更多的支配了大眾?並不是希望美化自殺,但這種社會給予的框架頗值得思考,至少應該給予尊重。
為甚麼那麼多自殺者親友對自己的哀傷閉口不提,不敢好好悼念,甚至要謊稱逝者到了外國?想要傳達生命正面的訊息,但在這個過程中無意傷害了多少人?理解自殺者親友的痛,讓他們好好面對他的哀傷不是最重要嗎?「甚麼為之『好』?『好』這個定義到底是你為哀傷的人定義,還是你自己的定義?」梁梓敦在採訪中道。


記者:符芷琳
《San Po Yan Magazine 新報人》
新報人(SPY)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生實驗報紙,以實踐新聞自由為原則;體現不趨附商業利益,不附從政治功利,只為專業學習的存在價值。

留下來的人不能磨滅的哀 自殺者親友難以啟齒的痛

生前無用死後有用 製造在世有用的「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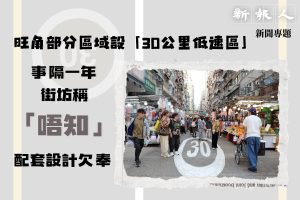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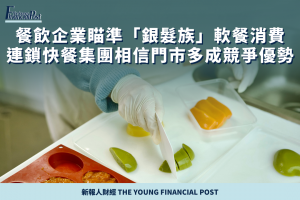


留言